|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1957~1965>反思:告别“工具”——读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 | 您好!今天是: | |
| · 历史反思 · |
|
|
| 作者:陈建华 来源:北大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站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魏承思,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学硕士。1980年代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并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1990年代起,先后担任香港亚洲周刊、明报主笔;亚洲电视新闻总监;成报总编辑;台湾商业周刊专栏作家。主要著作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佛教的现代启示』等8种;发表史学、佛学论文100多篇,新闻评2000多篇。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关门弟子。 可本站认为:尽管魏承思把1976至1989年称为“知识分子去工具化”时期,但这“去工具化”进程基本已戛然而止了,除了自觉意识、觉醒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继续沦为执政党的“工具”——更不用说许多原本已经入党的知识分子。而在2015年以来,更是一切“姓党”。此时,如仍能坚持“告别工具”、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还是有思想的大写的“人”,而非为一瓢羹而依附于某集团的“工具”! |
在汗牛充栋的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中,魏承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以下简称《沉浮》)无疑将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因为它写得实在──材料详实、立论平实、功底扎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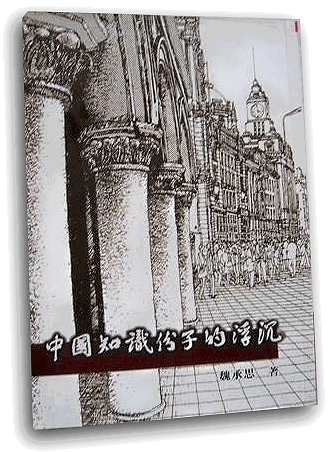 此书主要论述从1950到198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中国走向“全能主义政治”期间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集中探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本来就很少见,少见首先是由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克服的。
此书主要论述从1950到198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中国走向“全能主义政治”期间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集中探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本来就很少见,少见首先是由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克服的。
此书主要分三个阶段展开,即从1949至1957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1958至1976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确立”、1976至1989年为“知识分子去工具化”时期。在既有系统又突出各阶段重点的分析中,围绕典型事件和传媒人物,如“反右”运动中的《文汇报》、“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及邓小平时代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对于具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作了大量的采访工作,这些珍贵的口述数据为历史提供见证,亦体现了此书的社会史个案研究的独特之处。
将上海作为观察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窗口,确属明智的选择,却伴随着挑战。上海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无论对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文化的建构都举足轻重,而其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则万花筒般令人眼花撩乱。作者精练而概括地描述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列强并存、五方杂处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某种“创新、开放、多元、崇实”的“洋场”文化。尽管自二十年代末这一“现代化进程”遭到挫折,但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身份和传统并未完全丧失,他们对国民党专政的抵制充份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进入大上海之后,迅速而全面地进行了社会整顿。取缔妓女、打击奸商、镇压黑社会等措施,包括解放军不犯秋毫、露宿街头等,确实树立了“人民政府”的新形像,不光老百姓箪食壶浆,对于盼望统一、痛恨国民党腐败的知识分子来说,道德上似乎得到很大的满足。但事实上正如此书所强调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从一开始即具“全能主义政治”性质,已把矛头指向“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解放军进城伊始,就关闭了《申报》、《新闻报》等,下令停办一切新闻机构,其实是封杀言论和出版自由,已见先兆。由于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清洗和镇压运动,全社会弥漫着恐怖气氛,而在思想领域里也马不停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胡适、俞平伯,尤其是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上海知识界的打击更为直接。经历这几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已成瓮中之鳖、惊弓之鸟,更通过“自我批评”这一史无前例的模式,所谓知识尊严和独立人格都已丧失殆尽。(【本站注】还有令知识分子人人须书面交代、个个过关的自我解剖、自我作践式“向党交心”运动,知识分子已几乎“赤身裸体”示人。)
在分别描述这些思想运动时,我觉得更精彩的是,作者更深入到“全能主义政治”得以形成的机制内部,即细致勾画整个社会空间被化“私”为“公”,从工商界实行“公私合营”、国有企业“单位”组织到街道居民委员会、户口制度的建立等,党和国家力量控制了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经历了1957年“反右”之后,更加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生存状态”,无论在户口、就业、待遇等方面,都必须彻底依附于“单位”。精神上失去独立和自由与物质上的限制是一致的。且事实上“身”不由己,动辄得咎。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的名言:“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出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知识”也是换得吃饭之具,所以“皮”和“毛”的比喻表明一种雇佣关系。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无非要他们明白在新社会是“无产阶级”赐于他们饭吃。在这方面毛的逻辑其实同资产阶级又有何根本区别呢?富于反讽的是,如果说知识分子从前是附于“五张皮”上,但还有选择的余地,现在只有一张皮,而且吃的是“嗟来之食”!
在“彻底唯物主义者”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是被彻底“物化”的,其中已蕴含着“工具”论,这和他另一方面极端强调精神力量并不矛盾,即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无条件接受“马列主义”,即所谓“毛话语”。
正如书中叙述的,在1958到1976年之间,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工具,随着旧时代自由主义传统被扫荡殆尽,新中国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占领了文化舞台。在上海像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即为代表。他们为“毛文体”所“内化”。典型的如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当时“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方向标,其使用“罗思鼎”这一笔名,意谓在党的舆论机器中发挥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即把知识分子的“工具”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知识分子千人一面,万马齐喑,实即沦为毛字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沉浮》具有一种严谨而规范的学术风格。
作者先是就读于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师从“新左派”代表人物派瑞 · 安德森,深研西方各家知识分子理论。后来在香港大学攻读社会学,师从金耀基先生。如此书所体现的,历史感与社会学方法──系统分析、个案研究、实地采访——揉为一体。 (未完,接下页)
【相关链接】
| (本站 2013-12-13 编辑转发 / 2016-12-22 更新)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