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陋室文化>《新京报》记者/张悦:新中国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点击这里展开:简 介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又译为德兰修女、特里莎修女、德雷莎修女、泰瑞莎修女。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利亚裔,正如特蕾莎修女在去世前不久明确地告诉世人所言:“从血缘上讲,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从公民身份上讲,我是印度人;但从信仰上讲,我属于全世界。” 生于1910年8月27日(出生地:前南斯拉夫斯科普里),1997年9月5日因病逝世,享年87岁。 特蕾莎修女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奉献给解除贫困,而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Beatification)。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其他两位是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 特蕾莎修女去世,却留下了4000 个修会的修女,超过10万以上的义工,还有在123个国家中的610个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只有总统和总理才有资格享有的国葬,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后人赞她为: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2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 目前德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变为真福德雷莎修女(Blessed Teresa)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
|||
| 中国·武训 | |||
| (1838~1896) | |||
点击这里展开:简 介
武训先生(1838~1896),中国山东省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 武训原为乞丐,并无名。生于山东堂邑县武庄,自然随武姓,名“训”,则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 武训,是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培养和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被誉为“千古奇丐”。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 中国老一代著名影星赵丹曾主演过电影《武训传》。但1951年,毛泽东却发起了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的理论自然是所谓“阶级论”那一套所谓理论。赵丹也因此厄运连连……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
本站“重读历史”资讯:

| 新中国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
| 作者:记者/张 悦 来源:新京报/ 2004.09.09/新浪网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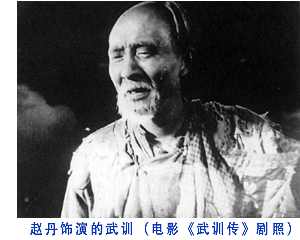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局面很快结束,电影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就是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批评被直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局面很快结束,电影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就是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批评被直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电影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治风险让许多电影人诚惶诚恐,电影的审查和管理也更加严格,当年没有任何电影投拍,电影产量严重下降。
§ 电影笔记: 追寻人民的记忆
1944年夏,陶行知送给电影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成就卓著的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孙瑜读了这个画传,便很快拟出简单的“剧情梗概”: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和创伤的武训,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不顾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下定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进行一场苦斗,坚持到底,终生不渝地、孤独地与社会作战,甚至是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
孙瑜读了这个画传,便很快拟出简单的“剧情梗概”: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和创伤的武训,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不顾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下定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进行一场苦斗,坚持到底,终生不渝地、孤独地与社会作战,甚至是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且让孙瑜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
1945年春至1947年秋,他第二次赴美,对美国电影做亲身观摩。在美国他一直带着武训的画传和“剧情梗概”,还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在域外的文化记忆中酝酿,在中外广阔的视野里,构成一部电影的轮廓。
1948年1月电影剧本成稿,当年夏便开始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拍,后转昆仑公司摄制完成。但令最初的孙瑜没有想到的是,这部《武训传》的编导创作过程,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算上出国前的第一稿,他先后写出五稿,又历经“中制”、“昆仑”两个电影厂,到1950年年底拍完,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这在当年公司遍地开花,一部电影只拍短短二三个月三五个月的情势下,是一个异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语境、外部世界在几年里变化太大了。外部的变动不居和内心的战争联接在一起,外部世界的力和反力永远同在。孙瑜睁大了眼睛,超越环境局限,追随到了深处,追蹑人民的记忆,关注并书写一个人的战争,并进而去关注更广阔的人生与更广阔的世界,关注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共同的问题、遭际与命运。
孙瑜对人生、对世界、对艺术的看法已不再是出于他个人的经验,而是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出于一种文化的审美选择。孙瑜创作中不是看重他个人的能力、剧情的故事性,而是像人性、人民记忆或真理、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念书能救人,这个人民记忆的真理在人性和文化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义上面对整个民族的塑造,它含有和寓示了更扎实的问题和内容。
孙瑜是名导演,他合作的演员不少是大明星,像阮玲玉、金焰、林楚楚、黎莉莉、陈燕燕、郑君里等。《武训传》演员阵容庞大,赵丹、吴茵、张翼、周伯勋、蒋天流都参加了拍摄。因为拍摄时间拖得很长,这部影片的两个主演赵丹、吴茵其间还合演了影片《乌鸦与麻雀》。一般人都知道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演技纯熟,但看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对赵丹的高度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都赞不绝口,称武训为其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演的武训,含泪微笑地默然跪劝小学生不要做赌徒;在牌坊下坚决不领皇帝赏穿的“黄马褂”……赵丹将人物不安宁的内心和那种永远地面对自己和与自己对峙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予以呈现。
武训要救孩子,“咱穷人偏要念书”,要他们上学,要上了学的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乡下人/庄稼人,“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一个人面对环境,面对外部世界,面对着种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与变故:火山爆发、冰川沉陆、战争、瘟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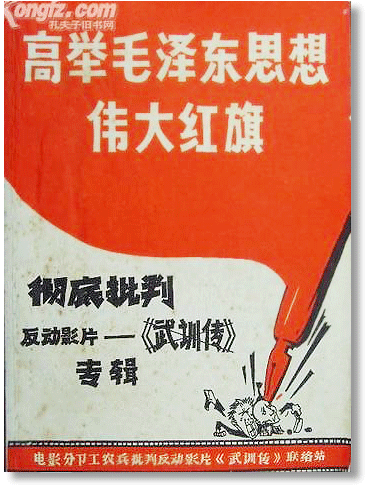 饥饿、非典、禽流感,可以与人携起手,并起肩,甚至全球化地去共同战斗;那么,面对无知、懵懂、文盲、不读书、怠惰,等等,就不能给予一点点启明,投入一种探索以至献身的意识吗?
饥饿、非典、禽流感,可以与人携起手,并起肩,甚至全球化地去共同战斗;那么,面对无知、懵懂、文盲、不读书、怠惰,等等,就不能给予一点点启明,投入一种探索以至献身的意识吗?
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模式。以公众福祉为目标,应该引以为我们内心的锲而不舍的力量。在《武训传》短暂的放映盛事之后,孙瑜、赵丹和一些受电影牵连的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1951年发生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这场批判,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其激烈程度与影响所及,也是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的。但是,电影家孙瑜和他的同仁不断由内心汲取力量,跨过这一段时期,仍然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在表达着自我,参与了历史和他的遭际。(丁亚平/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 被波及的其它影片
《我们夫妇之间》:独特视角遭批判
1951年,“昆仑”拍摄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影片《我们夫妇之间》。该片由郑君里导演,主演是赵丹、蒋天流。影片讲述上海知识分子干部李克与贫民出身的山东解放区干部张英结婚后,在许多事情上发生分歧最终重归于好的故事。影片大胆地提出工农兵干部面临着一个全面提高自己文化素质的问题,这种超前意识是它遭受批判的潜在因素之一。
该片同“文华”出品的《关连长》一样,在批判《武训传》的风波中遭到批判。有人提出这部影片“所选择的题材就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干部、共产党员的污蔑”等等。
影片的结局是从此便在影院中消失,而生产这部影片的厂家及主创人员感到惶惑不安,也使得私营厂众多创作人员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支持过影片的夏衍被迫在一篇文章中做了检查。不久,“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也被解散。(整理张悦)
▲ 对 话
“有什么缺点,也是电影艺术的问题”
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思想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持续了将近一年。对电影事业而言,这场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惨重的。记者就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武训传》”事件,采访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家孟犁野老先生,了解事件始末并为之深省。
最初公映受到普遍好评
新京报:孙瑜多年构思完成的电影《武训传》,据史料记载最初是受到肯定的,是吗?。
孟犁野:的确如此。最初“昆仑”的编导委员会多次讨论方案,并向夏衍汇报,夏衍当时坦率地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在目前情况下,不必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昆仑”还是坚持拍了。影片在1950年底全部摄制完成。在上海首映时,反响热烈。1951年2月,孙瑜带影片到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过后,除了认为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被人毒打的画面描写过长外,没有再提别的意见。影片在京、津、沪公映,受到普遍好评,报刊连续发表肯定和赞扬该片的评论文章有四十多篇。(本站注:孟犁野,曾任青海省剧协副主席、中国影协电影史研究部主任等,作家)
批判大潮汹涌而至
新京报:应该说影片公映不久,形势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吗?
孟犁野:是啊。过了不到三个月吧,当年的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指出:“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问题”,并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走到何种程度”,而且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战斗的共产党”。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短评,要求“共产党员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之后,全国范围内立即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第一次批判运动,持续将近一年。导演孙瑜和所有肯定过这部影片的有关领导以及文教界人士数十人,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讨。
§ 三十四年后重新评价
新京报:直到什么时候才对这场由批判《武训传》引起的运动予以重新评价的呢?
孟犁野:这是在1985年9月5日,大规模批判34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解放初期,1951年曾经发生过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并且还提出不论“电影《武训传》有什么缺点,首先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本站注: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任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京报:那现在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武训传》这部电影呢?
孟犁野:应该说《武训传》是一部在题材、风格上颇有特色的作品,但在思想的表达和艺术的探索上还显得不够成熟,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不过,作为政治问题加以“运动”式的批判显然是过分的。□ (全文完 新浪网摘编:小雪)
【本站后记】孟犁野先生最后对建国后第一场由毛圣上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声势浩大的思想政治运动(以及文艺整风、思想改造运动),只是说“显然是过份的”——这评价太客气了,太不着边了——因为即便是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也直言《武训传》“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了。
这场运动,扼杀和剥夺了应该特别有思想的群体——知识分子——思想的权利,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创造力,进而禁锢华夏国人整体的思想,这是使一个民族迅速退化的愚蠢,是犯罪。中国大陆大学众多,学者云集,享誉中外文学家艺术家也很多,但为何如曹禺、老舍、巴金、萧军等等,他们被称为名著的作品都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以后他们为何都再也创作不出作品或广受欢迎禁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为何即便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大陆堪称举世瞩目的原创成就寥寥无几?西南联大在那样战火纷飞的抗日时期能培养出至今彪炳史册的各类人才,为何直至2009年钱学森去世前还说“为何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冒尖’的人才”?
如此对思想言论的钳制、专制,使数亿华夏国人只须跟着一个人的思想走,绝对不许“旁逸斜出”(随其后还有“反右”“文革”);用进废退,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必将失去个体独立思考的能力——这,难道不正是“革”了一个民族精神和思考能力的“命”?一个失去了独立思考权利和能力的民族,能够“崛起”吗?
因此,对中共建政后第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思想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孟犁野先生用“显然是过份的”来作结,是不是过于轻描淡写了?
【前一页】 1 【后一页】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05-09-04 编辑转发 / 2021-03-10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