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陋室文化>应天常教授专栏>【学术交流】应天常:关于《节目主持语用学》答徐树华教授 | | 您好!今天是: | |
 |
本站其它链接
关于《节目主持语用学》答徐树华教授 |
■ 应天常(原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
| 撰稿:应天常 信息来源:作者赐稿 本站编辑发布 |
| 【说明】 2008 年4月,徐树华教授在他的新浪博客中发了一文,题为《应天常教授〈节目主持语用学〉中的几点可疑》。2016 年在“网海”中无意间读到此文,应天常教授觉得徐树华教授的问题值得探讨一下,写了如下文字以作答。(突出显示为本站所加,非作者所为) |
徐树华教授:
很抱歉,您2008 年4月8日的博文《应天常教授〈节目主持语用学〉中的几点可疑》刚刚看到,是我老弟无意间发现告知,算起来耽搁了8 年多时光。
其实,正是2008 年,我接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同意修订此书的通知。2001 年此书初版,存在诸多缺憾,我在修订本的后记中说“每每翻阅此书如芒刺在背”,如果修订过程中读到您的《几点可疑》,不仅对我修订此书大有裨益,甚至可向您讨教。总之,我的大意埋没了您的美意,然而《几点可疑》长期挂在您的网页上,我这古稀老人没有关注网海里的这一朵浪花,是可以原谅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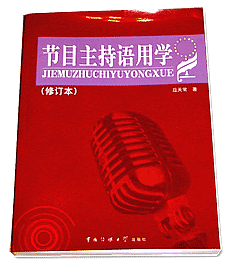 拙作初版面世以后,曾见到林兴仁先生(后来得知,他是陈望道先生的关门弟子)的书评,他对《节目主持语用学》的理论体系和语用观念作了正面评价,也准确地指出了几处“硬伤”。我特意将林先生的评论文章作为拙作修订本的“序言”。您尽管是“做课题的需要”研读了拙作的部分章节,发现了此书的可疑之处,也是十分可贵的,如果不是有违尊意,我将在再版此书时作为附录收入。
拙作初版面世以后,曾见到林兴仁先生(后来得知,他是陈望道先生的关门弟子)的书评,他对《节目主持语用学》的理论体系和语用观念作了正面评价,也准确地指出了几处“硬伤”。我特意将林先生的评论文章作为拙作修订本的“序言”。您尽管是“做课题的需要”研读了拙作的部分章节,发现了此书的可疑之处,也是十分可贵的,如果不是有违尊意,我将在再版此书时作为附录收入。
您提出三点质疑,放在一起说一点想法,与您交流探讨。
中国的语言学研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尽管索绪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过中国,却没有一所大学“敢”邀请他讲学,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在我年轻的那些年代,语言学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来“研究”的。八十年代,索绪尔、乔姆斯基以及查尔斯•莫里斯等人的著述才陆续允许引进。记得那时我在克拉玛依支边,有些著述还没有完全翻译过来,拦路虎太多,只能借助字典一知半解地阅读了。现在我们能很方便地检索文献、校正观点,是很幸福的。
拙作中关于语言分类的表述,确有不周,曲解了索绪尔的本意。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规范的整体”,当时我们肤浅的理解就归为静态“书面语”,而言语是进入应用领域就理解为“口头语”,显然是逻辑错误,是惯性的“概念平移”。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学术年会,张锐教授提出,我国既然将语言分为“书面语”“口头语”,可以参照索绪尔的界说分类,我后来轻率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严格地说,索绪尔语言理论建立的基础是语言、言语、言语活动,这三个概念开创了一个世纪的语言学。虽然它们的外延有重叠的地方,但这三个概念不是属种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这是我阅读索绪尔的理解。尽管其后各国语言学家都同意将这三者区别开来,但是对于索绪尔本人的区分及界说的看法,很不一致,至今仍众说纷纭。
我们的“概念平移”虽不妥当,也算是“众说”之一吧。
我以为,建立什么样的语言观,是语言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这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不易。比如索绪尔在语言本体的问题上有不少论述,但索绪尔的思想还不够明确, 他所指语言“是社会规范又是系统整体”,但是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是矛盾的。因为系统整体不是固化的,而是一个变量体系,所以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实际上更多的是建立在社会规范上,但是困境仍在于无法摆脱语言现实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差距,所以后来海德格尔坚持语言的本质不在语言之外,而在语言自身,他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言简意赅。因此我以为,语言本体论问题是开放的,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而要在考察全部人类思想和实存的“语言条件”的前提下追问,从这个角度看,索绪尔和海德格尔仅仅提出了各自的假设,而非语言本质的定论。
也许正因此,索绪尔没有将语言分为“书面语”“口头语”,这不符合索绪尔的语言观。比如朗读一篇文章,这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我们很快就会陷入悖论。索绪尔认为“文字表现语言”,就比较科学。由于现在播音主持业界都使用我国的传统语言观念,我在写这本书时,只能妥协,但是怎么论述这个问题,还需要斟酌。
关于这个问题,张颂教授生前和我有过一些探讨,究竟“书面语”“口语”“有声语言”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尤其是他喜欢用的“有声语言”这个概念,没有任何语言学著述用这个概念。我在深大任教期间,张颂来讲学,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认为,播音主持理论的概念体系混乱,需要厘清。但是张颂先生现已作古,我也垂垂老矣,如您有兴趣,欢迎参加这方面的理论建构。
至于您认为“牙牙学语”证明语言需要一个习得过程,这是肯定的,庄子也说过:“婴儿生无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
不过,您的质疑牵涉的是语言的起源,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语言是一个层级体系的音与义结合体,音与义处于最下层。“音”本来是一条混沌模糊的线性音流,人的呜咽哼哈、动物的啾咪嚎叫,分不出音的结构成分来;“义”也如此,混沌模糊,分不出意义的界限。因此,我的说法是“人类经过长达 6 万年之久的牙牙学语,慢慢学会把单个音节连缀成多音节的语句,并借以表情达意义,这就是‘口语’的出现,也是语言的诞生。”我以为,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而不是形式结构的命题。正是基于语言是音与义结合、约定俗成的“一种活动”,所以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一种摸索的过程。这里“牙牙学语”的“学”,不是“习得”,是摸索与练习。中国词语具有多义性,就好像“扶床学步”似乎不是孩子“学”大人怎么走路,而是摸索练习如何迈出步子走路。
我的这本关于主持人的语用著述,查尔斯•莫里斯的《语用学》、《符号学概论》是它的母本,尤其是符号学,我很看重,正是索绪尔最早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联系起来,他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这样语言学才在众多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语言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对索绪尔符号学遗志的继承,而从《语言符号学》到《符号语言学》是一个飞跃,它认为任何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都可以看做是“语言”。当然,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或特定载体与意义的关系)是由社会约定的,正因此,特定情况下的上课铃、鸣笛(比如两船交汇鸣笛表示礼貌问候)就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语言”了。当然,因为是单音节音义结合体,是处于符号语言层级体系的最低级层次,它们尚不能拆分组合,表达复杂乃至抽象的意义,但“拆分组合”不是符号语言的充要条件。
这样,动物有没有语言的问题,就比较好说了。虽然这是语言学研究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是正统语言学论述至今是回避的,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它是广义语言学或曰符号语言学范畴的课题。
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分标志之一是人能使用语言,我以为这里的语言特指“智能语言”。全球大约有 5000~7000 种人类语言,人类语言复杂细腻,无以伦比,但是大部分的科学家都认为动物有属于自己的“动物语言”(Animal Language)只是由于人类跟它们属于不同的物种,所以人类无法“听到”动物的“语言”。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年在日内瓦出版至今整整一百年了,值得纪念。他最早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联系起来,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需要后人继续探究的命题。
理论需要前进。
我们现在的语言学对语言的定义是人类自己出于本身和现有的认知对其的判断。我们不能以现在仅有的认知对未知领域做出轻率的界定和判断。这时,符号学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研究语言了。
现在语言学研究相当活跃,索绪尔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比如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曾说,语言的本质是交际,是交流信息、表达感情的方式。这个剀切的论断令人有彻悟之感。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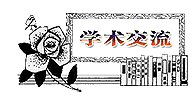 因此,查尔斯•莫里斯的语用学具有更强劲的生命力。基于此,拙作将语用学作为探究主持人语言运用规律的范本。
因此,查尔斯•莫里斯的语用学具有更强劲的生命力。基于此,拙作将语用学作为探究主持人语言运用规律的范本。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谈不上释疑,愿继续与您探讨。
再次谢谢您的批评。
应天常 2016 年8月12日
【相关链接】
▲ 徐树华:《应天常教授〈节目主持语用学〉中的几点可疑》(新浪博客)
▲ 简讯:应天常教授《节目主持语用学•修订本》2008 年出版
▲ 林兴仁:理论创新气息扑面而来——评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
(原载《现代传播》双月刊 2002 年第 5 期 )
〖前一页〗 1 〖后一页〗
(2016年8月13日编辑发布 / 2019-03-06 更新)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