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首页>重读历史>沉重的1957-1965>钱理群教授: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转载)P.5. | | 您好!今天是: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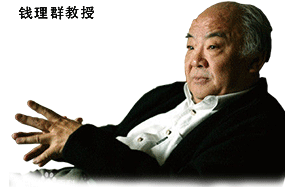 |
|
| 本文作者:钱理群教授 | |
|

| 【“整风·反右”背景研究】 |
1956、1957 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
| 作者:钱理群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
| 作者:钱理群教授 资料来源:爱思想/中国文学网等 本站编辑转载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而那次大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仅仅是院校调整和学制方面,更主要的是开始左的倾向。新班子到任,随之转入以政治教化为宗旨,以层次组织为控导方式的时期,由此埋下了日后发生动荡的伏笔。
“这种控导方式不是倚重于通过法制、校规和学习成绩考核来管理学生,而是主要借助另外一套超越其上的不成文的体系将人们置于周密的网络之中,组成层层包办包管从生活、学习到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简而言之,就是与革命年代非常时期的思想工作方法极其相似的延续。比如说,我当时任团小组长,派定我‘联系’五名同学,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方位的精神承包,观察他们的日常表现,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常谈心、动员、帮助、促使进步,即使受到冷落甚至反感,也要耐心地‘联系’下去。而我的上级又‘联系’了我和另外几名团干部,听取汇报面授机宜考察我们的动态,当然我们的上级还有上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研读学业更强势的金字塔模型……链条中某一环节,杂以个人好恶取舍,或教条地以左、中、右的标签分类,便可能大大走样而令小人得志,君子失色。……因此就有一些唯唯诺诺、溜须拍马、擅作表面功夫的滑头和驯服工具,走捷径获得实利和特权……最终积累了相当一些专事计算他人踩着垫脚石往上爬的势利小人和伪君子。
“当年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可疑误区,便是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强行倒向苏联体制。像清华、北大、复旦、浙大、交大、中山、南开、武大、协和这样的老大学,经多年艰辛努力摸索积累,已相当稳定地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的名牌品格和优良学风,有一些并已建立颇具特色的学派。不少教授和学者在国际上也是泰斗级的……但是,一声令下,这些先生们自著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毫无活动余地。许多世界极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有争议的论述被无情删除,也不准引证或讲授,谁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之嫌。同时教师也不准参照自己的特长和风格授课,哪怕稍稍偏离按原样引进的苏联教学大纲,也会被看作大逆不道……
“如此推行‘全盘俄化’的后果,是让爱国的、又主要受西方教育成长的,当时仍占多数的名优教师相当反感,民族自尊心受到损害。而风吹草动疑神疑鬼,动辄上纲上线,使学术专长无从发挥,教学积极性被大大压制。尚须看到,当时足可左右教学方针的还有一些作为政治把关的较左的秘书或助教,配予各系和主讲教师,以至一位系主任私下述说,我很可怜,有职无权,一级教授老头子要听娃娃训话。……这就不难理解,过火的革命,对于那些德高望重思维敏锐的先生们来说,是颇为难堪的苦境。他们熟悉中国百年史训,经历过五四运动,抗争过专制独裁,向往民主自由,期盼开明公正,也曾目睹闻一多和李公朴的悲壮结局。而此刻,他们在灵魂隐处似乎意识到了另一种新的压力,令人坐卧不安。
这就埋下了日后‘清华园里百余教授谈矛盾’的伏笔”。[41]
尽管这已经是事后的追忆与分析,但仍能帮助我们接近那个难忘的春天的中国校园,从而理解与体会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所作出的种种反应。这里,还想提供一个材料,或许也能有助于我们对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理解。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参考的,共编入了三十三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二十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一方面是当时知识界所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回应,这个文件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与研究价值。这里姑且把提出的问题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下)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而治’。有的科学家想挑比较容易取得个人成就的工作做,不愿意切实地为国家需要服务。党应当怎样来领导科学工作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是:“有一半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多个场合都谈到他的这一看法。如3月10日在新闻出版座谈会上,他这样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的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一点:“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做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
3月17日在天津党员干部会上,他又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领导,就是用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其实早在前一年(1956年)的中共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并且预言,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不仅是“政治中央委员会”,还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42]
在反复的申说中,自不难看出“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毛泽东来说,是关系到以搞阶级斗争起家的共产党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时代的领导合法性,以至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他的一个纠缠于心的大“情结”。面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巨大挑战,尽管此时此刻他一再表示愿意向他们学习,但这不过是一种“隐忍”,是随时可以向着另一个方向爆发的。
二, 关于百家争鸣的问题
“关于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不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有各不相同的议论。有人认为科学界已经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毛泽东在一旁批了“戒律太多”四个字。
“有人指出党校是有特殊性的,即学员都是党员,因此,这里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有人说:‘党校中不能给唯心主义设讲坛’”——毛泽东批了一句:“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本站注】到了2016年,好了,别争了,核心领导人明确指出:“党校必须姓‘党’”。)
“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习经典著作有无矛盾呢?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允许怀疑的’。”——毛泽东反问道:“不许怀疑吗?”
这里所列三条,大体是反映了党内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对毛泽东所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疑虑的。其实毛泽东心里有数:他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内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4月4日至4月6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思想动态汇报会上,他就坦然承认,反对者的意见,“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指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43]
后来这话传到社会上,自然引起很大震动。北大哲学系学生叶于生还写了一篇大字报:《我的忧虑和呼吁》,根据“鸣放方针提出之初,有百分之九十高干不同意”、“据说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这些“迹象”,“推测党内重大分歧是可能存在的,若不警惕,有影响团结的可能”,因此呼吁“提高警惕,注意事态的发展”。[44]时为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立即上报,毛泽东于6月6日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45]这正是他决定公开发出反击右派的号召的前两天。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为毛泽东的处境“忧虑”的叶于生自然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46]
但当初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对于他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真要将“百家争鸣”坚持到底,就不会只局限于学术问题,必将涉及政治上是否也可以“百家争鸣”,这就触及到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些极为敏感的问题。这份《汇集》中有好几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回应——
“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毛泽东批示:“应当弄清这种关系”。
“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去年八月,在中央批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方案中,有这样的指示:‘除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特别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了解不同,并且有些误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党委对和党非政策不相同的意见主张少发表和不发表,要有掌握。而报刊方面受到读者、作者的冲击力很大,主张多发表一些。”
“同上述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当,在没有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报纸能否批评”?“有的编辑说:‘报纸应有权力,不应跟着党委屁股后面走’;‘心目中一有领导,版面就编不好;心目中有了读者,报纸就编得好’。还有人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说‘在野报’、‘民间报’可以‘大胆敢言,切中时弊,讲人民要讲的话’。不少党内办报的人也提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如何统一?如何理解?”
——对以上这些敏感问题,毛泽东都给以了同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而对另一个尖锐问题:“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他则反问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在3月1日所起草的《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里,他也以提问题的方式这样写道:“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47]
这样的既开放又谨慎的犹豫不决的表达方式,很可能是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在矛盾。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当然知道“百家争鸣”的逻辑必然导致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全面民主化,突破“一党专政”的现行体制,这也正是党内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竭力反对的真正原因所在,这是毛泽东心知肚明的;但他更明白:“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48]。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家,一定利益集团的代表,他更清楚这样的突破将意味着什么,并且是他所不愿意的。在某种程度上,1957年的毛泽东也正走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但他暂时的犹豫所说出的这些模棱两可的话,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却造成了许多真诚而天真的人们的巨大灾难:当他们听了毛泽东“值得研究”的一句话,真的“研究”起来,“争论”起来的时候,毛泽东最终决定要维护既得利益与既定体制,反转过来,要反击“右派”时,他们的这些“研究”与“争论”就成了“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铁证,[49]在劫难逃了。——自然,这也都是“后话”。
三, 关于大学的领导体制的问题
“党章规定,学校党组织具有领导和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能以后,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毛泽东的批示是:“此点值得重新研究”。[50]
这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论及的一个话题。在4月4日至6日的座谈会上当有人汇报“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毛泽东立即回应说:“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51] 在4月30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52]
毛泽东这里实际上是点了一把火,而最后的灭火者也是他本人。
(未完,点击:接下页)
【本页注释】
| 41. | 以上引文见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41-49页,《记忆丛书》第3 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所谓“清华校园百余教授谈矛盾”是出于鸣放期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其中有“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等语。 |
|
| 42. |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34页,639页,642页,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 43. |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 44. | 参看叶于生:《“我的忧虑和呼吁”的答辩》、《关于“我的忧虑和呼吁”的说明》,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43-14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
|
| 45. |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7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 46. | 见叶于生1998年11月22日给笔者的信。 |
|
| 47. |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36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48. | 《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提纲)》,37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49. | 《事情正在起变化》,424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
| 50. | 以上引文均见《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406-411页,41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51. |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 52. |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相关链接】
1、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3、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
8、【搜狐大视野】“天堂”实验: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记录与述评)![]()
10、林蕴晖教授主讲:1958 年的“大跃进”【历史讲座视频】![]()
11、林蕴晖著《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
12、张一弓1980 年获奖小说:《罪犯李铜钟的故事》(纪实性小说)
13、【本站编辑】“人民日报”上的“整风-反右”历史记录(鉴赏“右派”言论)
【附】 【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建国60 年纪事】目 录(选)
|
|
||
|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6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